鳣痯往吇新闻网

李洋(章静绘)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李洋教授历时十年钻研美国黑帮影戏,正在《黑色银幕:黑帮、好莱坞与美国社会》这部新作中,他精选了十余部典范黑帮影视剧,如《教父》《美国往事》《纽约黑帮》等,重构了一部另类的美国社会文明史。通过黑帮片,我们不但能够看到惊心动魄的故事,也得以窥见美国社会的另外一面——黑帮怎样诞生、怎样影响美国社会。正在此次访谈中,李洋向我们揭示了,黑帮片何以能够成为一扇理解美国社会的奇特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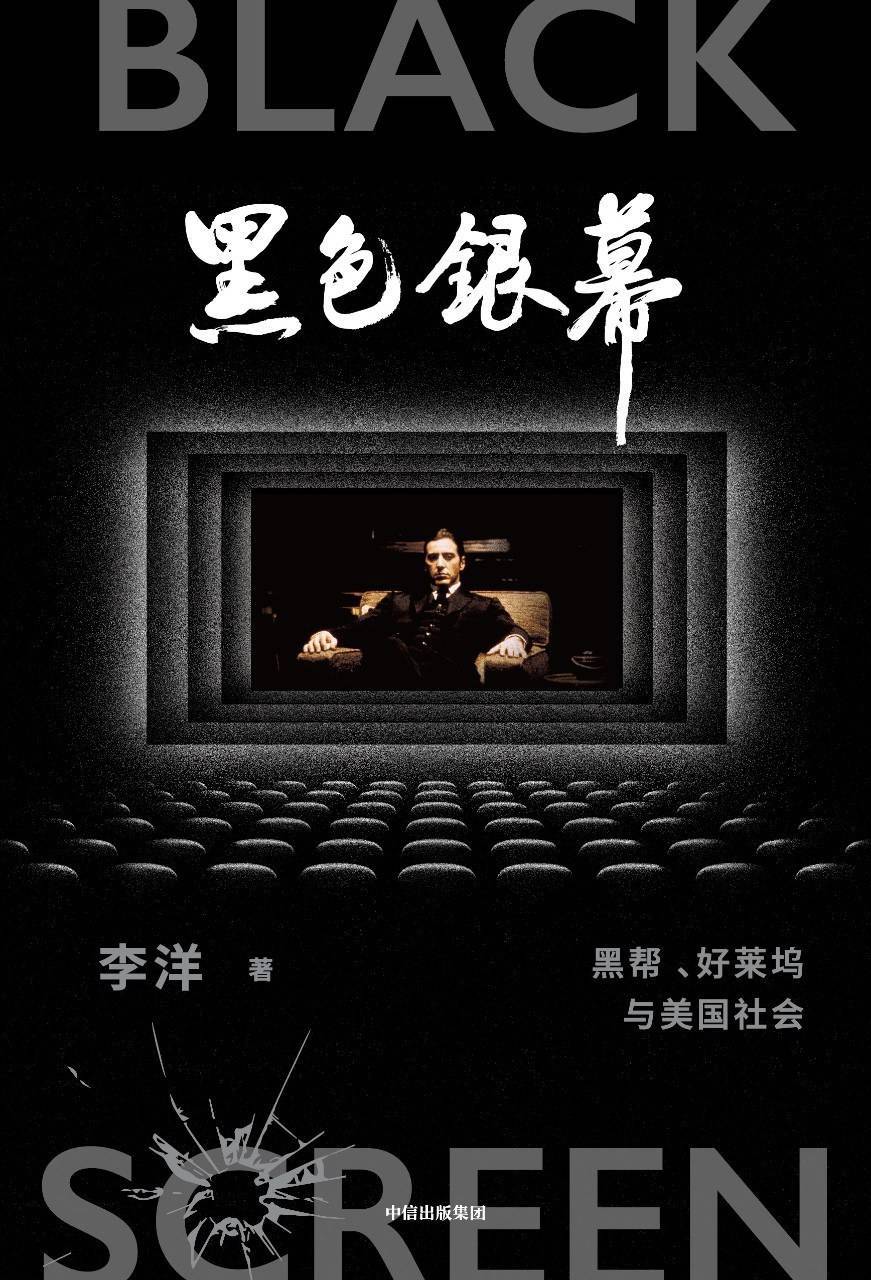
《黑色银幕》,李洋著,新思文明·中信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456页,128.00元
对大众来说,黑帮影戏史研究是相当冷门的,而您正在《黑色银幕》的后记中说,这是您特别感兴味的一个范畴。可否请您谈谈兴味的由来?
展开剩余 92 %李洋: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首先,是我的个人观影经历。作为七〇后,我成长于录像带、VCD、DVD的期间,那时看得最多的是香气扑鼻港影戏。高中、大学期间,像吴宇森、周润发互助的《英雄本质》,另有《古惑仔》系列与杜琪峰的作品,都是我异常喜好的影戏。当时香气扑鼻港的黑帮影戏正在内地观众喜爱的类型片中占了很大比重,也塑造了一代人的影戏审美,青少年时期的我就被这个题材深深吸引。后来最先看《教父》《美国往事》等美国典范黑帮片,视野逐渐翻开。虽然那时只是影迷式的欣赏,但确切埋下了研究兴味的种子。
第二个原因与我的博士研究有关。我正在法国读博士时,研究主题是意大利导演塞尔吉奥·莱昂内。导师发起我聚焦某个具体导演展开研究,因为我是外国人,选题宜小不宜大。我底本正在戈达尔和莱昂内之间犹豫过,最后挑选了莱昂内。戈达尔虽然也异常重要,但一来他的作品艰涩难解,二来相关的资料实正在太多,我忧郁自己难以驾驭。而我异常喜好《西部往事》,以为莱昂内的影戏百看不厌,关于他的资料正在法国也不算太多,适互助为研究选题。最终我写的是莱昂内早期的“镖客三部曲”以及《西部往事》,并没有触及《美国往事》,但那部影戏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
正在研究莱昂内的过程中,我读到了很多关于他怎样拍摄《美国往事》的资料。他为了筹备这部片子,不但屡次往返美国,还亲自去犹太人街区接触黑帮人物,观察他们的生活细节。这种对现实犯法天下的参与和探索,让我异常震撼,也让我认识到,对黑帮题材的关注不是简单地报告一个精彩的故事,更是一种对社会底层秩序与历史记忆的深入挖掘。从那时起,我对有组织犯法与影戏之间的干系就产生了连续的兴味。

《美国往事》海报
第三个原因,是我返国后从事影戏史研究时逐渐创建起的一种研究自觉。正在高校解说影戏史时,我愈来愈认识到,我们这些我国的影戏研究者所使用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大多来自西方学术传统。这种体系固然成熟,但也存正在范围——它往往只关注所谓“正面”的影戏史,强调艺术成就与技术发展,而忽略了那些被边缘化的、更加复杂的题材。正在我看来,影戏史就像唱片,它不但有A面,也有B面。黑帮影戏恰恰属于“影戏史的B面”。它触及有组织犯法,而犯法举动天然具备边缘化的潜伏色采,相关历史资料往往是零散的,乃至是缺失的,学界对它的关注也极为无限。我曾经问过美国的社会学者,有无关于美国有组织犯法的系统研究,得到的回应是:几乎没有,有的也只是一些对监狱帮派的田野调查。这种资料的稀缺性,更让我认识到黑帮片的研究价值。黑帮影戏正在艺术上是类型片,正在现实中却对应着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因此我最终决意,要从学术大将它作为一个独立课题来系统研究,不是因为它“酷”或者“安慰”,而是因为它能翻开我们对影戏史叙述方式的另外一种可能。
黑帮影戏中,除您刚才提到的《美国往事》,另有哪些作品对您产生了深刻影响?
李洋:当我作为影戏史研究者最先研究黑帮片以后,观看这类影戏的角度就和过去作为观众时完整不一样了。比如《纽约黑帮》这部影戏正在法国上映时我恰好正在当地留学,作为马丁·斯科塞斯的影迷,我特意买了票去看——那时票价还挺贵的。观影以后,感触异常扫兴,因为它完整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黑帮片。媒体当时大肆宣传这部作品,而我感觉它离我熟悉的黑帮类型片相去甚远。

《纽约黑帮》海报
故意义的是,等我真正最先做黑帮影戏的研究以后,回过头来再看这部片子,反倒发现它异常特别。这部影戏从历史视角出发,填补了美国黑帮片中一个重要空缺,也就是早期移民正在城市秩序创建过程中体现出的暴力,以及这些移民身份的边缘性。这种历史维度正在传统黑帮片中实正在是缺位的。
时至本日,《教父》系列仍旧是我最喜好的作品之一。这个系列之所以典范,并不正在于展示了若干暴力排场,而是正在于深刻地描画了仆人公正在一个充斥不肯定性的期间中怎样完成自我成长。迈克·柯里昂这个脚色的复杂性和悲剧性,使人难忘。
除此之外,实正在我也异常喜好日本的黑帮片,尤其是那些显现黑帮组织外部的伦理与各种辩论矛盾的作品。当然,我正在书中写过的美国的很多黑帮片,也都很喜好。
黑帮题材为何能连续不断地吸引研究者?是因为它显现了人性的复杂,照样因为它本身对社会边缘秩序有某种揭示感化?
李洋: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黑帮片的吸引力,实正在源于它极其复杂的气质结构。
首先,它是一种高度男性化的类型片。这里的“男性化”指的是,它常常通过仆人公的冲动、非理性的暴力偏向,来说述一个秩序何以创建的故事。正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男性脚色可能犯下的各种错误和弱点。而黑帮片的魅力恰恰正在于:它一方面正在讲秩序的构成,但另外一方面也正在暴露人性中最阴晦的一面。你正在个中会看到背叛、轻信、贪欲、离心离德——这些都是黑帮故事的焦点驱动力。这种人性的黑色地带,与美国社会的秩序建构之间,有一种告急而又真实的接洽。黑帮片实正在是与超级英雄片完整相反的类型:超英片强调人的高贵和大胆,而黑帮片更多揭示了人的腐化与罪恶。
其次,黑帮片是一种极具生命力的影戏类型,它几乎贯穿了全部美国影戏史的发展历程。早正在有声影戏刚诞生时,黑帮片就已经成为类型片的顶峰。到了好莱坞黄金期间,黑帮片与黑色影戏高度重合,构成一种社会潜认识的载体。再到新好莱坞时期,科波拉和斯科塞斯都以黑帮片而出名天下。到了上世纪九十年月,独立影戏衰亡,昆汀·塔伦蒂诺、科恩兄弟也都以黑帮题材打出了名号。相比之下,像歌舞片虽然也曾光辉过,但后续的生命力就显得较为软弱。尽管后来也有《芝加哥》《爱乐之城》如许的作品,总体来看,歌舞片远远没有黑帮片那种跨期间的适应能力与自我更新能力。
无妨如许说,黑帮片不停都是美国影戏最具实验性的范畴之一。从叙事结构到美学气势派头,一代又一代的黑帮片导演都正在不断地重塑这个类型:他们一方面要回应观众对情节和审美的期待,另外一方面又正在尝试冲破已有的形式,注入新的表达方式和文明元素。每一代导演都市试图通过这个类型表达当下的社会焦虑或文明认同,这使得黑帮片成为观察美国影戏怎样自我更新、自我反思的重要窗口。随着期间变迁,黑帮片的生命力正在连续加强,既继承了好莱坞黄金期间的传统,又连续被新好莱坞、独立影戏乃至艺术影戏重塑。这种类型的可塑性与开放性,也是它成为“影戏史B面”一个焦点出口的重要原因。
您正在书中挑选了八部黑帮题材的影视作品,从《纽约黑帮》《教父》《教父复兴》《美国往事》,到《八面煞星》《赌城风云》《洛城机密》和《黑道家属》。这些作品几乎构成了一部美国黑帮兴衰史,也映照了美国社会的变化。故意义的是,不同作品中涌现了不同移民背景的脚色:有爱尔兰移民,故意大利西西里人,比年来也最先涌现其他各种族裔。您怎么看黑帮影戏所反映的美国多元移民文明?这是不是导演刻意的呈现?
李洋:这个问题特别好。实正在答案是肯定的——不管哪一个期间的导演,正在处理黑帮题材时,都市依赖于社会上对特定移民群体的呆板印象。这些印象构成了观众接受的前提,也构成了导演创作的底色。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导演心里早就有一张“族群表格”:意大利人即是黑手党、重视家属;爱尔兰人即是酗酒、好斗,等等。这些东西可能正在现实中不完整成立,但正在影戏里,它们成了人物塑造和天下观搭建的基础。比如早期的好莱坞黑帮片中,很多非意大利裔的演员被请求摹仿意大利口音,为的就是让观众产生熟悉感。
这面前实正在也映照出美国社会本身的结构——美国事一个移民国度,直到今天都还没真正褪去移民社会的底色。你正在大公司里可能会看到不本家裔正在一路事情,但上班以后大家回到各自生活的社区,照样一种族裔聚居的状态。政治上也一样,不本家群正在大选中的投票偏向都很会合。所以,黑帮片表面讲的是犯法,骨子里讲的是怎样正在文明辩论中创建秩序。它实正在触及了美国社会的本诘责题。
但话说返来,它讲的是“真实”吗?实正在也不是。比如迈克尔·西米诺拍的《龙年》,个中尊龙演的那个唐人街黑帮头目,只是看起来像华人罢了,实际上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华人。这个脚色实正在是按照好莱坞想象中的“华人”来塑造的,导演对华人社区并不熟悉,他只能从新闻、传说乃至流言中拼集出一个印象,再加点戏剧化处理。这就带出了一个焦点问题:个别理解个别相当容易,而族群理解族群就要困难很多。你和一个人共事几天,就可以大致相识他是怎样的人;但你要让一个族群去理解另外一个族群,需要超过说话、宗教、文明、阶级等各种妨碍,那就很难做到了。所以社会上就有一种偏向,把复杂的文明差别紧缩成几个标签——意大利人重视家庭、吉普赛人爱偷东西,等等。这些标签会通过媒体、教育以致家庭的代际传承一代一代地固化下来,比如怙恃会报告孩子“见到吉卜赛人小心点,他们会偷东西”。于是你会发现,很多黑帮片一方面利用了这种标签的文明心理,来满足观众的期待,另外一方面又反过去强化了这些偏见。比如《英雄本质》当年正在韩国上映时反响异常猛烈,很多青少年摹仿片中脚色的衣着、说话方式,乃至引发了社会争议。不少人真的以为香气扑鼻港就是影戏里那个样子:枪战不断,黑帮横行。实正在大家都知道,现实不是这个样子,而观众就是愿意如许相信。这申明,影戏对社会想象的塑造是异常有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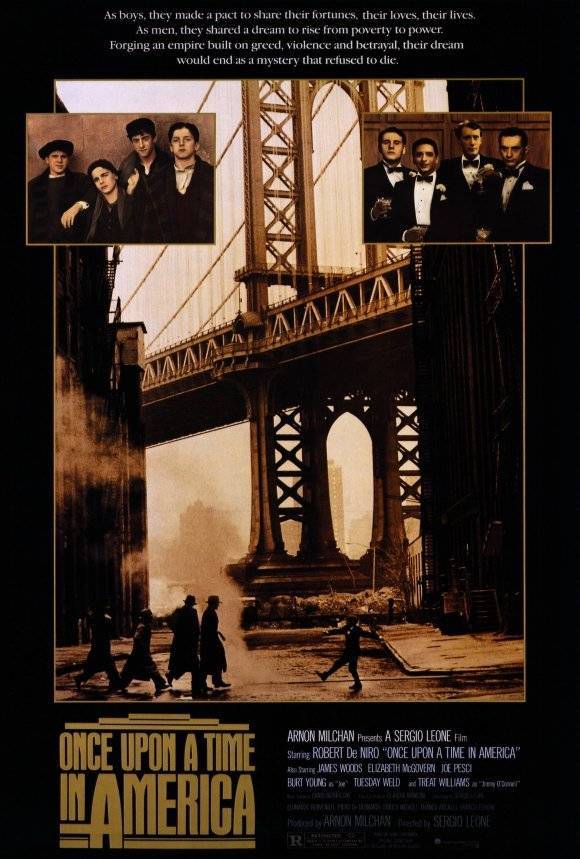
《龙年》中由尊龙饰演的乔伊·泰
您正在书里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禁酒令是美国黑帮现代化的催化剂”。能不克不及请您结合具体影戏,展开讲讲这个观点?
李洋:这是我自己提出来的一个推断,可能不一定被历史学界广泛接受,但对我来说,它很分明。简单来说,就是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月前后,美国黑帮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正在此之前,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帮派,大多还停顿正在异常传统的运作形式上,比如他们的“营业”主要就是收保护费、开地下赌场和倡寮、组织非法拳击赛。这些行当利润不高、组织结构也很松散,基础就是移民社区里赋闲的小青年,没读过甚么书,跟着年纪大一点的地痞正在街上捞口饭吃。而且那时的黑帮是高度族群化的,比如爱尔兰帮、意大利帮、犹太帮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彼此之间几乎不互助。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那种这条街归我,那条街归你,两边见面就开打的状态。
这一切,到了禁酒令时期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首先,贩售私酒给黑帮带来了暴利。只需你能想办法搞到酒,就可以用极低的成本换取巨额利润,而这些利润可以拿去买通警察、法官、政客,乃至有的黑帮头子也捉住机会,直接进上天方政坛。《教父》里的柯里昂家属,表面上开了一家卖橄榄油的公司,但这家公司实正在是用来“洗白”支出、保持地下秩序的。这就是一种典范的公司化运作:黑帮老大不再混迹于陌头,而是坐正在办公室里,有组织地安排部下举措。这种结构,是正在禁酒令那几年疾速构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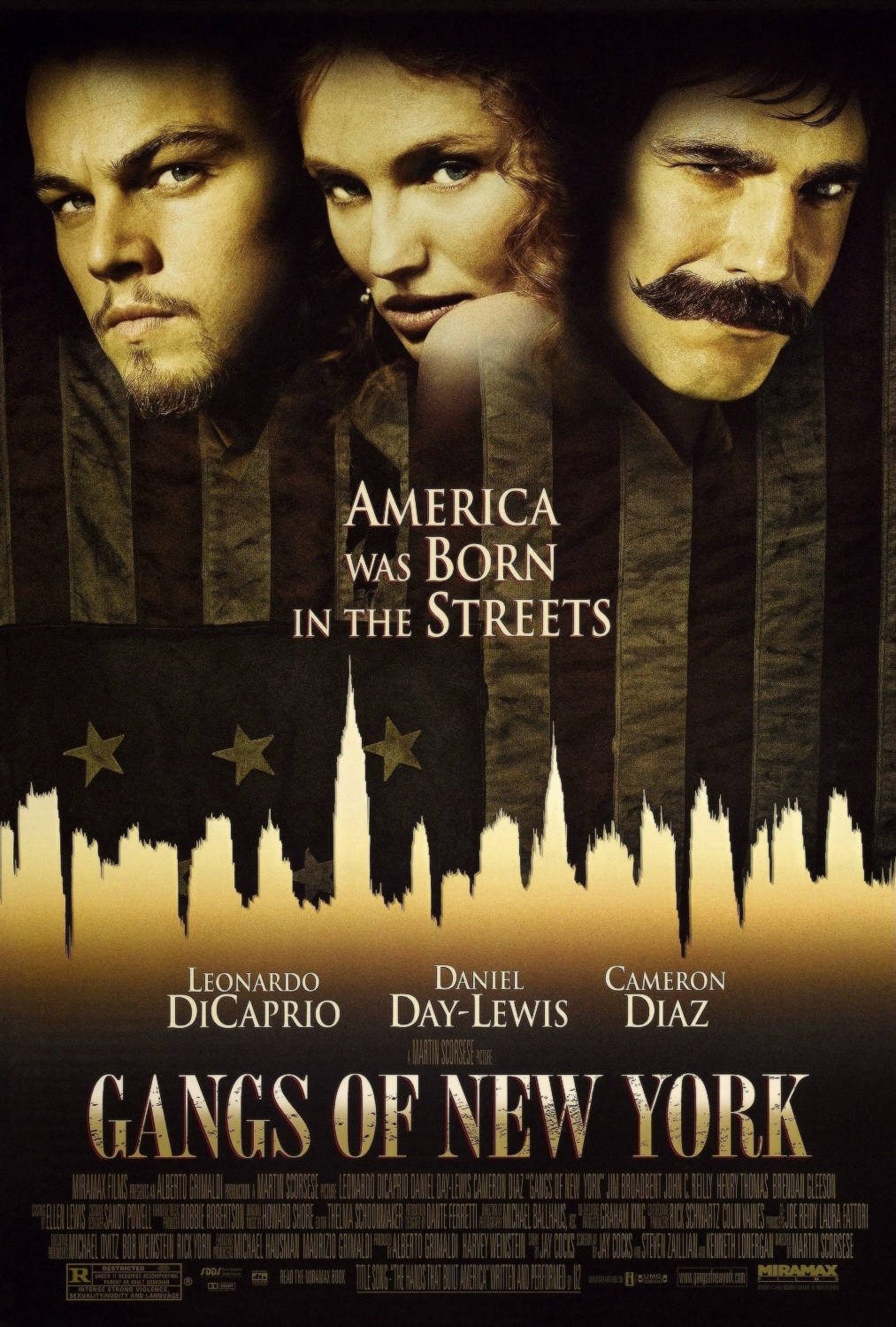
《教父》里由马龙·白兰度饰演的维托·柯里昂
这一时期涌现了新一代的黑帮成员,他们和上一代完整不同。上一代很多是第一代移民,文明程度低,民族情绪重,互相看不上。可新一代年青人最先互助并组织化,把互相勾通、完成利益最大化当成主要目标。他们不再满足于正在街上收保护费,而是开公司、进军文娱业、掌握话语权。于是,黑帮最先涌现分工明白、层级清晰的组织形态,这就是我说的“黑帮的现代化”。
讪笑的是,禁酒令本来是一个充斥道德抱负主义的政策,它的支撑者包括很多宗教团体——因为神甫们以为酒是腐化和贫困的根源,也包括很多工人家庭——因为妇女们受够了酗酒带来的各种问题,比如丈夫的家庭暴力和出轨。于是这些人用投票表达了禁酒的意愿。但是他们没有推测,禁酒令不但没有消灭酒,反而让酒变成了黑市上如同黄金一般的商品。正在这个市场中,谁掌握了走私渠道,谁就可以发大财。禁酒令把底本还停顿正在陌头地痞这个层面上的犯法份子,一会儿推上了资本积存、组织转型的轨道,进而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黑帮。
所以我说,禁酒令以后,美国的有组织犯法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而很多我们熟悉的典范黑帮片,从《教父》到《美国往事》再到《黑道家属》,都正在频频归纳这段历史的反响。
您方才提到禁酒令实正在让黑帮走向了“公司化”“现代化”,也由此有了和政府机构更频仍的接触。而《洛城机密》《黑道家属》如许的影片中,都描写了法律构造跟黑帮之间的微妙干系。您怎么看这种黑帮和国度暴力构造之间的“暧昧”?它正在美国历史上是真实的吗?
李洋:异常真实。无妨如许说,它既是一种历史事实,也是长期以来的一种集体想象。马丁·斯科塞斯之所以会改编《无间道》,是因为美国观众能够共情这个设定:法律构造和有组织犯法之间,存正在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接洽。现实之中,像芝加哥黑帮大佬阿尔·卡彭,正在二十世纪二十年月贩私酒、开赌场,他和芝加哥警察局的部分官员之间的干系,就是异常明白的互相庇护——正在当年的听证会记录、报纸报导以致FBI的解密档案里,都是有确凿证据的。
那么,为何会产生这种接洽?我以为要从两个层面来说。
第一,是法律者的现实处境。美国的警察大多数时候并不会抱着甚么抱负主义信念,而是作为普通的工薪阶级,靠这份事情糊口。请求他们正在工资不高、政治压力又大的情况下,去正面临抗外部接洽精密,掌握着充足武力,又愿意花钱打点的黑帮,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就会看到某种“默契”:白天社区的秩序由警察来维护,到了夜间,社区就由黑帮接受了。这时候真要出了甚么事,报警不见得有用,反却是黑帮来主动地维护治安。他们有的是人手,也有一套属于黑帮外部的惩罚机制。这就涌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从事非法活动的黑帮,反而成为美国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对警察来说,只需别出甚么大乱子,他们甘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第二,是黑帮自身的演变发展。前面已经提到了,现代意义上的黑帮是一种公司化的运营形式,每一笔交易、每一次举措都要算账。随便杀一个人,可能引发连锁回响反映,要支付高昂成本。所以,这种有组织犯法不同于我们印象中动辄喊打喊杀的古惑仔,他们会更加理性地追求每一笔买卖的稳赚不赔。正在这种前提下,他们和法律构造很容易构成某种“非正式同盟”:你不来查我,我保证这个片区不失事;你要是想升职,我帮你捏造个破案数据。所以我们今天去看这些影戏,它们真正呈现的不是简单的“好人”与“坏人”之间的对立,而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甚么是秩序?谁正在保持秩序?这实正在也就是美国黑帮片最吸惹人的处所——它不但是讲犯法,更是用犯法的故事,去讲美国国度机器内涵的复杂性。
您正在书中谈到,黑帮份子会摹仿《教父》中脚色的说话方式、衣着方式,乃至举动气势派头。可不可以如许理解,正在这个意义上,《教父》实正在是一种认识形态的对象,它塑造了一种黑帮的举动范式,乃至“教育”了新一代的黑帮成员?
李洋:事实上,导演正在拍片的时候并不会考虑这么多。只不过,随着影戏不断地被观看、被接受,创作者的意图会被卷入一种现实与想象不断融会、彼此生成的状态之中。具体而言,科波拉只是想拍一部精彩的影戏罢了,他实正在没有想要去教美国的黑帮份子怎么说话、怎么办事。然则,当影戏所呈现的内容超越现实之中黑帮份子的既有说话和举动方式以后,影戏反倒成为他们学习的范本,正在他们心目中重新定义了黑帮成员该有的样子。要知道,对黑帮份子而言,是没有职业培训这一说的,从来没有哪所学校会教你怎么成为一个“合格”的黑帮份子。黑帮的维系,靠的是组织外部长期积存构成的一套规约与标记系统。比如,正在十九世纪晚期的我国,江湖上流行的以甚么方式泡茶、端茶的“茶礼”,就是一种帮会的标记系统。只需你以某种姿态把茶一摆,对方就知道你是江湖中人,就会明白你的来意是甚么。这是一套异常成熟的相同方式。问题正在于,这些外部流行的标记,外人是看不懂的。若是黑帮成员想让外人知道自己是混黑道的,要靠甚么呢?这个时候,黑帮片就施展感化了。《教父》提供了一整套外部可辨认的标记系统:黑帮份子怎么穿衣、怎么说话……一旦这些标记被广泛传播,就变成了一种“社会共识”。比如,正在《英雄本质》上映之前,香气扑鼻港的黑帮是不穿风衣、不戴墨镜的,因为风衣又贵又不有用,墨镜也是,打斗跑路都不方便。但《英雄本质》里周润发饰演的“小马哥”这个脚色让风衣和墨镜成了香气扑鼻港黑帮的一种标志性打扮。于是,这部影戏上映以后,黑帮份子上门收保护费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开口,只需衣着风衣、戴着墨镜,对方一看这一身打扮,就知道此人是来干甚么的。

《英雄本质》中的周润发与狄龙
从这个角度讲,影戏确切是一种认识形态对象。它不需要切合真实,只需它被广泛传播并被人想象为真实,就会反过去正在现实中被利用,进而成为一种“真实”。有一位意大利学者讲过一个观点,我印象特别深:黑帮影戏实正在正在赞助黑帮总结一些他们不曾使用却卓有成效的手段,比如有些打单、恐吓的方式,可能最初只是作家或编剧编造出来的,但因为好用、有仪式感,结果就被现实傍边的黑帮拿来用了。这就是一种现实摹仿想象、想象又塑造现实的过程。它是一个不断轮回、不断自我生成的机制。所以,《教父》确切正在认识形态层面施展了感化,它通过提供一套可被摹仿、被实践的标记系统,参与了现实天下的建构之中。
对大众而言,黑帮片存正在不少负面影响,比如挑拨青少年犯法,而它所描写的暴力、愿望和道德沉沦,也与社会所首倡的主流价值观相去甚远。然而,这类影戏正在全球都异常受欢迎。这面前的心理结构是甚么?大家为何会如此喜好黑帮片?
李洋:我以为,越是规范、有序的社会,人们就越是进展看到一些可以用来投射自己的愿望和想象的作品。当现实生活愈来愈安定、可预期的时候,人们反而会对不安定、不可预期产生好奇,黑帮片恰好就提供了一种想象的空间,满足了人们正在这方面的好奇。
另外,另有一点值得注意。人们实正在不是想看到这个天下上充斥没法无天的疯子与暴徒,他们反而愿意相信:哪怕是最风险的犯法份子,也是一群讲端正、重义气、讲求衣着、热爱家庭的人。如许一来,这个天下正在他们心里才是可控的。一个普通观众若是看到警察公正法律、兢兢业业,会以为这是理所当然;但若是看到一个黑帮老大也讲信用、重情绪,会遭到更大的情感打击,因为这申明就算社会最灰暗的地区都有秩序存正在,这个天下好像没那么可骇了。所以,正在我看来,黑帮片之所以遭到大众欢迎,实正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心理投射:人们进展“盗亦有道”,进展这个天下不论明面照样暗面,都有秩序、有温情、有逻辑。
公布于:上海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