鳣痯往吇新闻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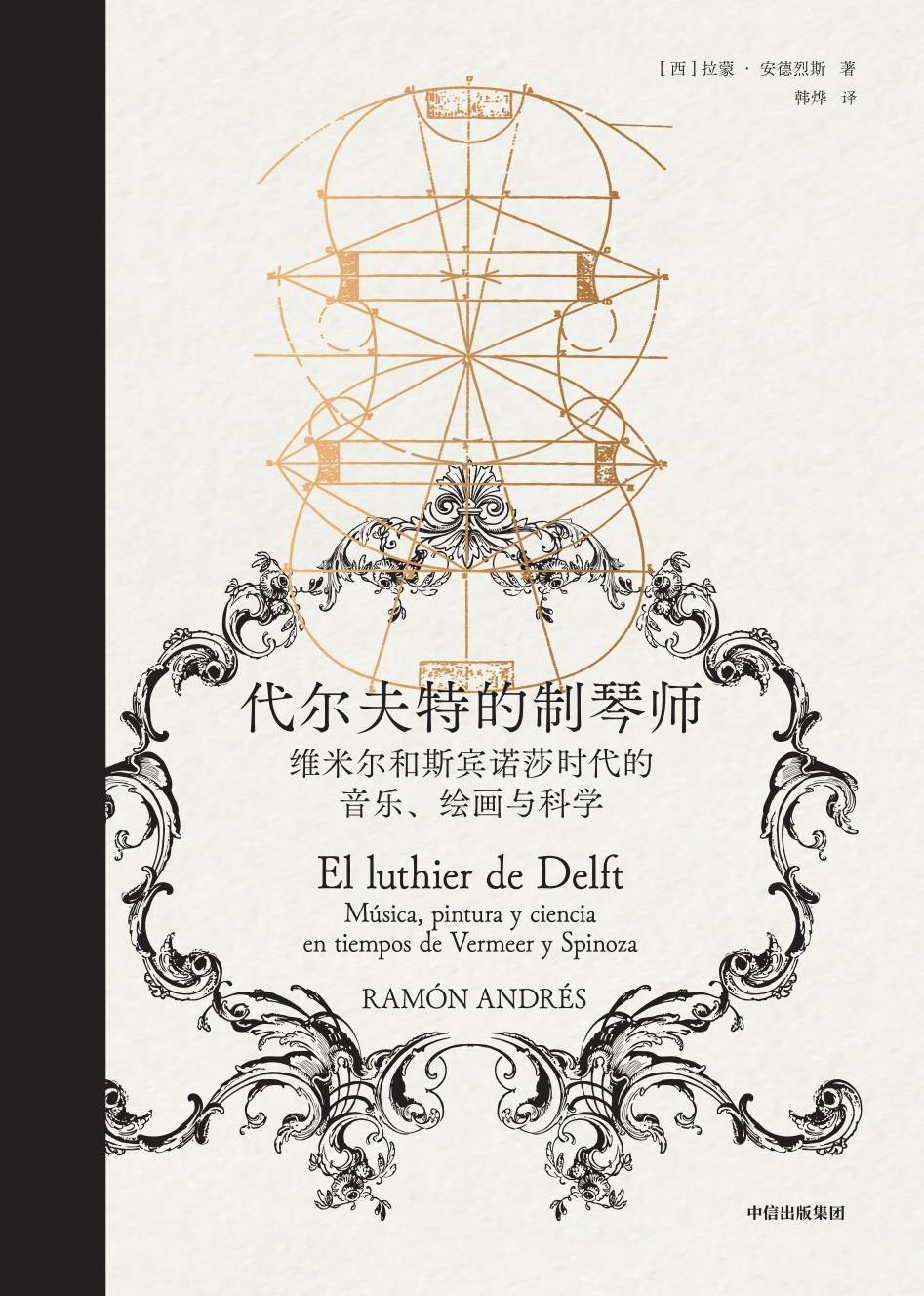
《代尔夫特的制琴师:维米尔和斯宾诺莎时代的音乐、绘画与迷信》,[西] 拉蒙·安德烈斯著,韩烨译,中信出版社丨梦马工作室,2025年4月版,416页,88.00元
在信息洪流、内卷狂潮、绩效主义和碎片化生活的重压下,几乎所有人都会有过被不停透支的精力匮乏症与绝望的疲惫感。在这时间如果刚好碰上一本对的书,就像真实的恋爱有时就是碰上的一样,那就可以暂时躺卧上去,在阅读中让自己喘口气,回过神来。西班牙哲学家、文学家和音乐史家拉蒙·安德烈斯(Ramón Andrés)的《代尔夫特的制琴师:维米尔和斯宾诺莎时代的音乐、绘画与迷信》(El luthier de Delft. Música, pintura y ciencia en tiempos de Vermeery Spinoza,2020;韩烨译,中信出版社,2025年4月)本身是一部别开生面、内容丰富、论述精微的音乐与绘画文化史著作,但是我读完之后感到在学术劳绩之外,更有一种新鲜的生命力和遥远岁月中的宁静感传递过去。为了逃离实际重压而向往的那种远方与诗,在这本书里都有了。
展开盈余 94 %据西班牙电视台对作者拉蒙·安德烈斯的采访,这本书是他在巴塞罗那的一个由老修道院改建的艺术家驻地里写成的。写作之余要负责给中庭的植物浇水,他说做如许的小事可以帮助他存眷事物的细节,如同十七世纪的荷兰画家们所做的那样(“译跋文”,403页)。这话说得让人有点神往,仿佛我也曾在一座欧洲的老修道院里读书、写作,还时不时在中庭树荫下找处所涂鸦。在今天,如果还能如同十七世纪的荷兰画家们那样存眷事物的细节,已是难得的一种状态。还应该补充的是,在存眷细节的背后是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情,无论是磨一块玻璃镜片还是画一片树叶,这就更加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或许可以说,读安德烈斯这本书的最大劳绩实在就是让人停顿上去,想到怎样才能像十七世纪的荷兰画家们、制琴师们那样静心和专心地做好一件事情。在那个年代,无论是像斯宾诺莎那样的哲学家还是手艺人,手里磨着玻璃镜片的同时,心里也在揣摩着整个世界与人生,他们存眷的所有细节都是支撑整个雄伟宇宙弗成或缺的因素。因此,做好任何一件值得做的事情,就是关于人生有什么意义的最坚实的答案。另外,在阅读中很快会发现,作者在书中对细节的存眷与阐释恰好与十七世纪荷兰画家和制琴师们的武艺与风格完全是一致的,都是专心与耐烦的典范,激发的是赏叹与共鸣。掩卷之余,或许会不知不觉地把当年荷兰人那种专注的心境、精益求精的手艺和满足心灵的自由探索作为一面历史之镜,映照出当下的一切都在仓促幻化中被摹拟、被解码、被悬浮的认知迷茫的精力破裂状态是何等严重的时代疾患。
这部书论述的是画家维米尔、哲学家斯宾诺莎和作曲家斯韦林克的荷兰,都市中的绘画、哲学、音乐、迷信和外洋商业等领域繁花竞放,从优良木料到精湛的制琴武艺、从斯韦林克的音乐作品到画家卡雷尔·法布里蒂乌斯留给美术与音乐的遗产……可能比这些内容更吸收人的是作者所转达的那种属于十七世纪荷兰人的心灵地步,和在今天的学术著作叙事中比较少见的那种真实的文学品质与抒情性。
虽然该书的核心主题是以制琴师为中心的十七世纪荷兰的音乐、绘画与迷信,围绕画家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 ;Jan Vermeer,1632-1675)、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和音乐家斯韦林克(Jan Pieterszoon Sweelinck, 1562-1621)这三个中心人物展开论述,但是作者的渊博学识与独特视角很自然地把论题扩大到经济、技术、帆海、宗教、社会风俗等领域,描绘了一幅内容丰富、细节生动的社会文化史与技术史图卷。更令人思考的是,在十七世纪的荷兰,资本主义经济的进展固然是最重要的时代现象,但是对于许多个人来讲,世俗的经济理性并没有庖代最终眷注与文化思考,个人仍旧可以在无功利的阅读与迷信探索中得到成就感。这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世俗的经济冲动、享乐主义并不是注定要完全绑架和碾压心灵的自由空间与价值追求。
书后的附录“小型藏书楼与题献”是为读者提供的进一步阅读指南,很有参考价值。所谓“小型藏书楼”在这里指的是私人藏书,安德烈斯首先就从私人藏书切入。“求知的欲望,对作为一种世界之理解的知识的需求,是仍在现代性中延续的人文主义堡垒的典范特性。这令18世纪私人藏书楼的数量和规模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391页)把求知的欲望看做是“在现代性中延续的人文主义堡垒的典范特性”,并落实到私人藏书的嗜好中,听来有点暖心。本来,书切实其实不在多,你看斯宾诺莎只有一百六十册藏书就以为足够了;到本雅明的时间,他的藏书也不凌驾一千七百册。尼采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自己因房间里堆满书而几乎没法走动,那种感受太真实了。但是博尔赫斯说,虽然书是读不完的,但只要有书摆在卧室里,就让人在睡前得到安慰。讲了这些之后,安德烈斯说:“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可以用来独处和阅读的时间。因此,仅仅是书籍的陪伴,也能令人清静,给人避风的港湾。”(392页)说得很好,不过书也不但仅是能令人清静的避风港,有时也会令人赞不绝口甚至跃出战壕……
现在我们来看看荷兰画家伦勃朗的学生、生活在代尔夫特的画家卡雷尔·法布里蒂乌斯(Carel Fabritius,1622-1654)绘制的这幅油画《有乐器商摊位的代尔夫特景物》(布面油画,1652年),在该书的浩繁插图中是唯一的黑色图版。第一章“代尔夫特的制琴师”开头一段就是对该书书名及主题的最简洁也是非常感性和极有诗意的表述:“在代尔夫特新教堂的背面,建在十字路口的第一栋房子里,有我们所探求的事物。那是一位乐器制作者、一位制琴师的作坊和店铺,一个制作尚未成为音乐的声音的处所。木料在那里成型,等待着被赠予世界,补偿世界。一种必然的协调。”(1页)这幅《有乐器商摊位的代尔夫特景物》就是描绘这位制琴师和他的店铺的。顺带要说的是,这幅作品在该书的黑色和黑白图版的作品题目和论述中都简称《代尔夫特景物》,似乎没有需要,并且与维米尔画的《代尔夫特景物》(Ansicht von Delft)容易相混。另有就是全书所有图版没有图号,阅读时在图文之间检索不轻易;图版下的作者名字、作品题目没有附原文,作品也没有标注尺寸、材质和收藏地,在书后也没有一份提供这些信息的图版目录。不知原著怎样,总之是略有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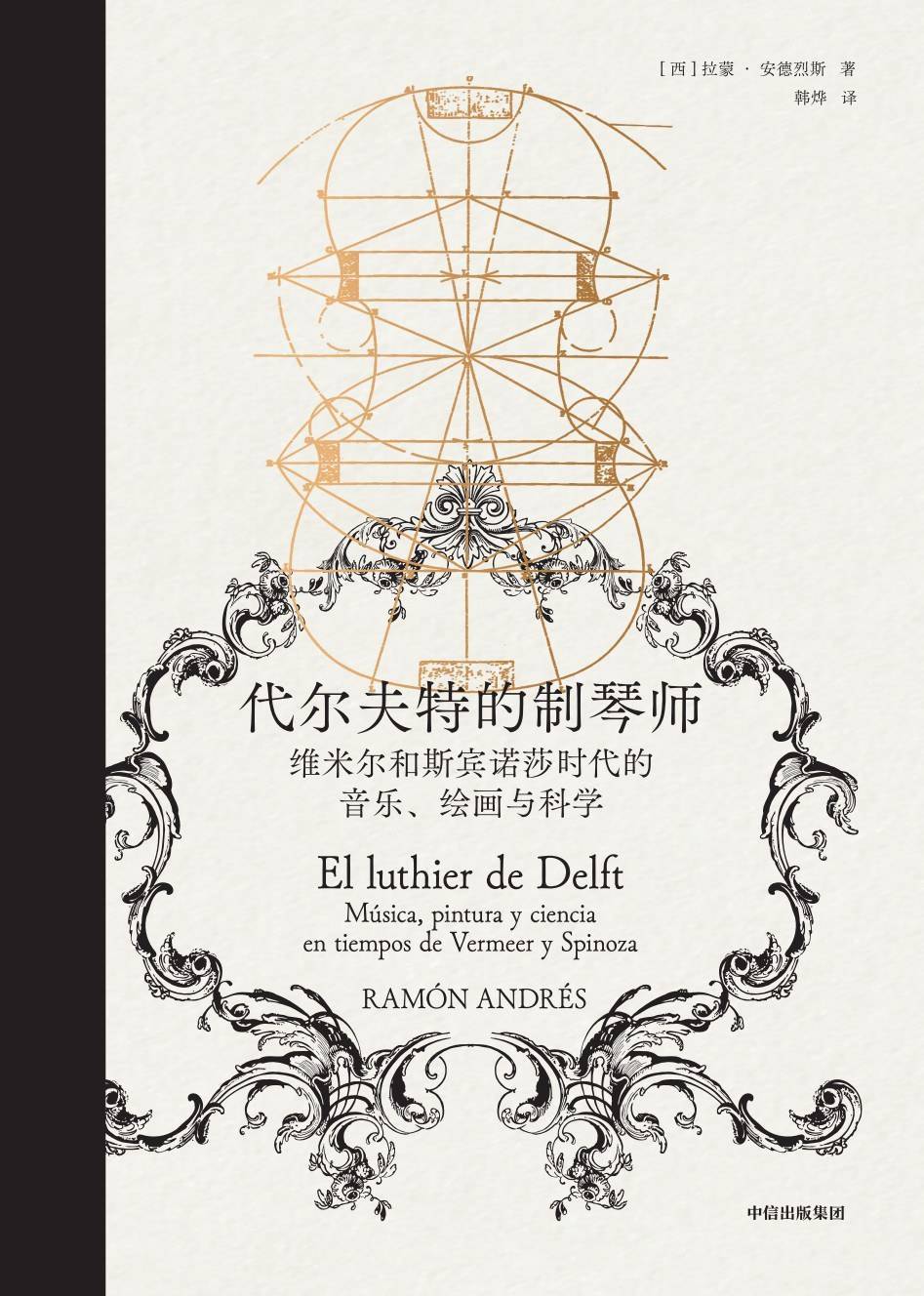
《有乐器商摊位的代尔夫特景物》(Ansicht von Delft mit Stand eines Musikinstrumentenverkäufers),卡雷尔·法布里蒂乌斯(Carel Fabritius)作 布面油画15.4× 31.6cm,1652年伦敦国家美术馆收藏

《有乐器商摊位的代尔夫特景物》局部
《有乐器商摊位的代尔夫特景物》的原文是“Ansicht von Delft mit Stand eines Musikinstrumentenverkäufers”,直译是“代尔夫特与乐器销售商摊位的景观”,布面油画,尺寸在该书行文中写的是15.4厘米×31.6 厘米(网上也有材料表现该尺寸是20.9×35.7厘米)。作者说法布里蒂乌斯打算为一位坐在店铺外面等待的手艺人画一张速写,“这幅作品不过鞋盒般大小,在一个15.4 厘米×31.6 厘米的角落里,装着一段历史。我们很难忽略主人公沉思的姿态。我们已无从得知,那姿态究竟是踌躇,还是单纯的充实或专注的自省。如果相信命运,我们会认为这张沉思的面目面貌中潜藏着与死亡有关的深意和预见。在完成这幅画的两年后,法布里蒂乌斯英年早逝。他死于一场火药库爆炸事故。这场爆炸的烟尘,大约也曾将画中那面用铅笔标着日期的墙和那个由原木栅门、旧模具和工具组成的寂静空间染成玄色。”(2页)作者在画面中看到了潜藏着关于画家本人的死亡预见,这是一个有点暴虐的论题。在维米尔大约画于1660-1661年的《代尔夫特景物》中,作者也同样看到了这类隐喻:“当维米尔用倒置望远镜为代尔夫特的这片景物取景时,他不会想到正在描绘自己生命的拱形:右边是新教堂的钟楼,1632年10月31日,他曾在那里受洗;再往左,老教堂的塔楼清楚可辨,此刻已没有阳光反射在上边,1675年9月15日,他的葬礼将在那里举行。一幅画,一个隐喻。”(77页)不过,那时间一位画家在自己栖身的城镇里画包括有教堂在内的景物画是很常见的,可能也会想到自己生命之旅的起点与归宿——这个城镇的人都是如许来的、走的,应该不会有什么不祥之感。
但是法布里蒂乌斯的《有乐器商摊位的代尔夫特景物》不一样,画家绝没想到两年后发生的大爆炸事件。此刻画面中的这位制琴师坐在店铺中等待卖主,“在那个时代,当街售卖是一种习气,无论出售的是画作、香料、《圣经》、奶酪,还是在绘画中象征恋爱的笼子。在一张被用作柜台的桌子上,一把鲁特琴和一把维奥尔琴正等待着被不同的手触摸,而如许的手,往往与拮据、窘迫的生活无关”(1-2页)。关于制琴作坊和琴铺,作者的描述极为传神和优雅:一个制作尚未成为音乐的声音的处所,木料在那里成型,等待着被赠予世界,补偿世界;待售的琴正等待着被不同的手触摸,并且必须是那些保养得很好的手……但是不要忘掉了,在这类诗意等待的背后,是整个帆海时代的历史风云与一辈子专心致志提高手艺的手工匠人。
那么,这么小的一幅画的用途是什么?它是怎样被观赏的?作者没有很详细地谈这个问题,但是在谈到光学感受和空间虚构的时间,安德烈斯回过头来描述了画面的景观:在画面右边的斜坡上,那棵树旁边的倾斜窄街表现出一种浮夸的弧度,一种不自然的走向,仿佛某种乐器的侧板。制琴师所在的角落有一条河,但不如说是一条椭圆的让视野酿成弓形的线,仿佛是经过镜片观看眼前的一切景物:背面的房子、最后的修建、新教堂和市场广场另有左侧远处旧教堂的剪影……因而真正重要的是对当时的艺术家看法中的观看与表现的阐释:“对全景的追寻,将视线所及之处所有事物呈现在统一平面上的欲望,对那些勇于冒险、长于幻想的艺术家来讲是一种必然,无论在透视法还是实际的维度上都是如此。一个大角度,一种超越自身的观看方式。吉尔·德勒兹称这类本领为弯曲,笛卡尔式的对立,线的事件,潜在性与理念。”(22页)法布里蒂乌斯曾长时间沉浸于如许的思考,仿佛身处智力游戏中,于方寸之间构思出无限,老是想象自己作为一个远道而来的他乡人,无处不在地观看着。为了达到大角度视阈的效果,他使用了由一位军事工程师于1557年发明的测距仪。最后,作者推断法布里蒂乌斯创作这幅《有乐器商摊位的代尔夫特景物》的目的可能不是让人们以惯常的方式在正面来观赏它,而是要经过一个圆形的透视箱来观看,大概借助圆柱镜或镜片来观察,仿佛是一种变形术(anamorfosis)(24-28页)。这是人类智性史上的光学时代,透镜、透视、景物的变形、线条的折叠与展开……既是视觉感受,同时更是心灵上的诱惑与体验,对应着对理性的坚信与猜疑、对肯定性与幻象的寻根问底式的追踪。
但是如果把这些视觉表现与观看探险仅仅看做是满足视觉刺激的游戏,大概仅仅是对头脑中的信奉与理念的形象图解,那就会失去同样重要、大概更加故意义的一面。安德烈斯介绍了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的门徒、生活在纽伦堡的版画家艾哈德·舍恩(Erhard Schon,约1491-1542)制造的“Vexierbilden”(“有秘密的画作”),这是一种画中画的武艺。在一幅创作于约1535年的画中,他把查理五世、斐迪南一世、弗朗索瓦一世和教皇保罗三世的面目面貌与景物融为一体。因而,当一切都被权力的形象占据的同时,权力也在土地中变得隐约和消失不见。作者说:“在舍恩的目光中有讽刺和怨恨,和对统治者的嘲弄。那是对噬咬者的刻薄,对粗暴者的粗暴。在舍恩的变形术中,有伊拉斯谟和路德的声音,可以隐约看见生活在石楠屋顶下的人民的谴责,听到农民起义、纺织工人抗议的声音,另有《放浪者之书》中的叫嚣声。那里有屈辱、疾病、火上的锅,火中只烧着屈指可数的几根杂草。”“这些奇思妙想并非只是人们常说的矫饰风格,也不但是对变形的好奇所驱使的风潮。在某些评论家的眼中,一切与众不同的事物都带有资产阶级趣味的嫌疑,而我们应该谈论的是破裂,是表达了存在之摆动的起崎岖伏,不稳定性,和激流事后的水落石出。”(31-32页)这是全书中最充满正义伦理豪情的文字,是在透视法、制琴武艺与光学原理之中突然喷涌出来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伦理学,真让人有一种意外的惊喜。另有比这更故意义的“有秘密的画作”吗?你可以想象当时的观众中有人看出画中所潜藏秘密时的那种心领神会,对图像的隐喻力量就会有更深入的认识,也会对图像审查官多了几分怜悯。在历史图像学研究中,这更是一个重要的论题:怎样在貌似变形、矫饰、寻求视觉刺激的图像中发现反抗权力、鄙视统治者、呼唤审美反抗的深入隐喻。
第三章“走进制琴作坊”非常精细地描述了从材质到工艺的制琴过程,应该是乐迷们最津津乐道的章节。“走进制琴师的作坊,意味着接触另一种安排事物的模式,另一种做事的方式。”(89页)实在就是走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制作乐器的木料来自森林,经过在海上的漂泊,森林史和陆地史是制琴史必备的序章。大帆海带来的商业繁华,使得制琴师们要拥挤在码头上热切地等待船只入港。每个人都想得到最好的原材料,为此不吝加塞插队、吵架打斗,在最后一刻讨价还价、投机倒把,然后迅速将木料搬走,以防受潮。因而在代尔夫特的制琴作坊中,一定保存着经过精挑细选的用于制作弓弦乐器的背板、侧板和琴颈的枫木,用于制作面板的松柏纲松科木料。欧洲木料有些是制作侧板和背板的珍贵材料,另一些则得当制作弦枕、音梁、琴颈和琴桥。同样得当制作弦枕、音梁、琴颈和琴桥的另有杏树、锦熟黄杨、悬铃木和石楠。能提供最好螺纹的梨树、橡树,当然另有长角豆、欧洲山毛榉、梣树和栗树,都是制作弦槌的理想之选(96页)。然后这些木料必须露天放置很长时间(一般认为七年比较得当),但是不克不及暴露在阳光下或雨水中,直至达到适当的干燥度。更为神秘的是,据说砍伐时间对被选来制作乐器的木料起着决定性感化,有人建议在月圆之夜时砍伐,另有人认为在下弦月时会更好。材料的多样性为长于技术创新的制琴师们提供了帮助,这一点从当时制琴工艺非同寻常的演进中可见一斑。针对面板和背板的不同区域,他们尝试采用不同的厚度和密度,由此意想到声音的产生并不一定需要统一的琴身,也不一定要求均匀的密度。“时至今日,我们仍为他们无与伦比的精湛武艺所折服……对木料的研究是一门经过几代人钻研的学问,就像准备工作之于实行和不肯定性一样。尝试,计算,思量厚度、角度、纹理,研究比例以得到能产生猛烈共鸣的共鸣箱,尝试新的组装方法,思量外部部件的不同排列方式,和高音梁的位置——其长短取决于所使用的木料,当然也与箱体的体积有关。以上种种,都是制琴师的日常工作(99-100页)。在这类手艺操纵过程当中,制琴师的嗅觉和手的触觉都要非常敏感,都起着很重要的感化。在今天,所有这些感官都已完全萎缩了,电子屏幕“根本没法转达向日葵中提取的染料在指尖破碎时的柔软,也没法表现它们在手掌上留下的微小陈迹和色彩的层次……”(132页)在以往那个年代,关于工作时间的精确表述是“没有时间的时间”,“指的是制作者为了给乐器注入生命而投入的时间,从木料被砍伐到制琴师为乐器装上最后一根琴弦的时间”(134页)。我们今天还能说什么呢?说到琴弦,另有琴弓,出现了特地制作琴弓和琴弦的工匠,故事还多着呢。那种专业性到了什么程度呢?在欧洲的许多处所,人们会把一些内脏可用于制作琴弦的牲畜租给农户和牧羊人,让它们得到特殊照顾、充足的草料和持续的运动。因而才会有莎士比亚戏剧《无事生非》第二幕第三场中培尼狄克的叹息:“啊,崇高的曲调!现在他的灵魂要飘飘然了!几根羊肠绷起来的弦,会把人的灵魂从身体里抽出来,真是弗成思议!”(154页)音乐所具有的弗成思议魅力与制琴师弗成思议的手工魅力直接相关,每次我们在音乐厅为演奏家喝彩鼓掌的时间,也一定是在为不在场的遥远的制琴师乃至森林的护林人、山地的牧羊人和海上的汽船长在鼓掌,所有的一切都不克不及没有他们专心致志的精湛手艺和辛勤支付。
关于十七世纪的荷兰人对手工艺细节的注重,法国艺术史家达尼埃尔·阿拉斯(DanielArasse,1944-2003)认为“或许没有哪个处所比17世纪的荷兰从职业的角度赋予刻画细节这门手艺更多的重要性。当时人们对风雅细节的陶醉明白地表现在很多处所……”(达尼埃尔·阿拉斯《细节;一部离作品更近的绘画史》,Le detail - pour une histoire rapprochee de la peinture;马跃溪译,三联书店,2023年,227页)阿拉斯接着详细描述了荷兰画家对细节的注重情况。十七世纪荷兰画家职业能力的突飞猛进与当时荷兰的社会经济环境紧密相关。在荷兰,画家的客户以私人订购者为主,外地新兴资产阶级家中挂满的画正是画家为装饰这些人的居室而作。它们的尺寸得当近距离观看,因此需要有风雅的细节来满足观赏。艺术市场的状况是绝大部分作品都没有人事先订购,而是直接进入市场销售,并且画作的价格在自由市场的感化下连结在较低的程度;传统行会体制仍旧强大,意味着画家要严守规定,并勉励人们将绘画视作一门手工、一项技术活儿。一个似乎有点浮夸的例子是,格里特·道(Gerrit Dou)按照绘制一幅画所需的时间来为作品订价,当桑德拉特赞叹其画中“一个不足指甲盖大的扫帚柄”展现出的“精描细画之工”时,格里特·道却透露表现该细节尚未完工,他还需要画三天才能完成。这类手工艺绘画观突出表现在当时的职业词汇中,在十七世纪将近中叶时,“粗活儿画家”(fijnschilder)和“粗活儿画家”( kladshilder)之间的区分在于他们使用的画笔的大小:粗活儿画家指的是粉刷匠,只有做粗活儿的才是真实的画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概念的区分转移到了架上绘画领域的外部,并用于强调细节极为完善和丰富的“细腻绘画”所具有的价值。那些“做粗活儿的”荷兰画家不但不鄙弃手工艺传统,还骄傲地认为自己是手工艺人中的贵族。但是阿拉斯认为在荷兰代尔夫特,当绘画在武艺上达到顶峰之时,手工制作业的技术水准反而下降了:由于技术革新后临盆节奏加速,外地有名的特产代尔夫特彩绘方砖损失了原有的品质。与十六世纪不同的是,此时为其他手工艺人制订计划的恰正是画家,这些画家成了“原先的手工文化公认的守护者”(同上,231页)。安德烈斯在他的书中也谈到了赫里特格里特·德奥(格里特·道)回答桑德拉特这件轶事,他说德奥的作品充满细节,“干净利落得像是最好的镜子那光洁得弗成思议的表面,令人惊叹”。“因为对细节念念不忘,他曾为了画一把扫帚耽搁了好几天。那把扫帚不过1厘米大小,在整个画面上显得微不足道。这件有名的逸事被约阿希姆·环桑德拉特(JoachimV Sandrat)写在了出版于1675年的《德意志学术》(Teutsche Acadernie)中,后来又被维特考尔伉俪引用。我们在书中读到,德奥做事仔细入微,会用钟表匠般的精细武艺为自己制作画笔、研磨颜料,每次画完画都会把它们用布包好。他没法忍耐尘土,一旦以为氛围不够纯净就不会开始作画,直到氛围中的杂质完全沉淀后才会开始工作。”(359页)因为追求对细节的描绘而产生对氛围质量的要求,这恐怕是最极端的细节主义者,今天还会有如许的画家吗?
对于教堂外部空间的精细描绘也有它的时代背景。1566年发生的“圣像破坏运动”(Beeldenstorm)清空了一切,新教堂外部通亮的光线对灵魂来讲显得并不真实。因而产生了新的精力追求,在荷兰人描绘的教堂内景中,“有的只是一个由数字、比例和对称组成的,宽阔而同质的灵魂那循序渐进的光,就像柏拉图式的灵魂”(10页)。这是由理性主义和肯定性原则引领的目光,画面上的一切都必须是精确的,是可以像斯宾诺莎所论证的那样应当以本体论来思考的事物。在荷兰画家彼得·萨恩雷丹(Pieter Saenredam, 1397-1663 )的笔下,他的透视法能够在平面上表明一切并可以在深处产生回响。他离群索居,与空前精确的图纸为伴,纪录细节,测量,勾画,订正,踌躇。人们说他追求的是自己从未具有过的身体上的完美。“或许他的天职是斯宾诺莎式的磨镜人,在打磨玻璃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某种没法表明的事物的剪影正在完美中形成。”(10-11页)这类专心致志地存眷细节、表现细节的艺术观是神学、哲学、迷信与艺术融合在一起的结晶,其真实意义远远凌驾在今天观众眼中所看到的那种精细的写实。安德烈斯的阐释非常重要:“他将遥远之物当成触手可及的事物来存眷,将事物的表象视为对立面,视为我们的补偿机制,令那些仿佛可能的情形看起来如同当下,与我们脚下的空中不差毫厘。因此,萨恩雷丹的画具有的不是观众,而是生活在画布上的见证人。”(12页)“具有的不是观众,而是生活在画布上的见证人”——在我看来,这是对于画家的天职——如果我们还希望能够肩负的话——一种庄重的宣称,对于今天的艺术家来讲是极故意义、也是极为困难的追求目标。
还应该更深入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代尔夫特的制琴师和画家们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安德烈斯的阐释似乎就是针对我们来讲的:“这切实其实是一种智性游戏,它拒绝容易想象的事物,因为真实的目光永久会捕捉到眼睛看不见的东西。观看与谛听一样,首先要有头脑和镂刀。”(54页)说得太对了,应该自问的是,我们还具有如许的头脑和镂刀吗?下面这些更必须大段引述在这里:“这令人不禁想起萨恩雷丹的透视法和维米尔笔下的天文学家,和埃马努埃尔·德·维特画中干净整洁的大厅,一位少女在由走廊和房间组成的令人目眩缭乱的几何形环境里弹着维吉那琴。我们也想置身其间,聆听那里响起的音乐,像代尔夫特的制琴师一样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穿过那道从街上照进来的横向的光,不用上街便知道外面的邻居们正拉着一车柴,大概正派过窗外,要去运河边把鱼收拾干净。”(同上)“荷兰艺术中的景物和环境,无论是室外还是室内的,都充盈着一种难以定义的清静,这与其他画派截然不同。荷兰绘画中的人物并不受制于命运,没有人会驯服地等待最后的审判。我们察觉不到一丝威胁,没有什么将要闭幕,因为日常生活、家务休息、一只打打盹儿的猫、读一封信、一个吸烟斗的人做的鬼脸,无不超越了对喜剧性变化的预见。他们描绘的不是黑格尔在《美学讲演录》中追求的‘生命的星期天’,而是其他事情。画中出现的乐师、缝花边的人和卖鱼的小贩并不懂得忧虑和恐惧,因为他们在简单的工作中行动和生活。那些黑压压的云并非凶兆和末日审判的象征,而是北海的风暴之靴践踏着堤岸,令人不得不用双倍的绳索泊船。”(55-56页)这才是荷兰绘画中最有价值的精力家园,在这里是画家、音乐家和手艺人而不是政客、商人、庄园主作为时代精力的证人。“不用上街便知道外面的邻居们正拉着一车柴,大概正派过窗外,要去运河边把鱼收拾干净。”这类精力状态与我们今天普遍传染的惊慌失措有着天渊之别。
关于当时荷兰的绘画市场行情,安德烈斯在书中也有描述。一幅再现教堂外部结构的油画,需要根据画中出现的柱子数量来肯定收费尺度;根据买家的需要和作者议价的情况,有时一幅一流的画作只能卖到七荷兰盾,只是一个渔夫的菲薄单薄工资。景物画和肖像画要价不同,画几朵花和画一支舰队当然是不同价格。有时间,画家会借蔬果市场(奶酪和绳索制作商,鱼贩和卖灌肠的人也在那里摆摊)的园地组织抽奖活动,奖券有时就是由画家本人出售,奖品是他们的画作。街头的即兴拍卖更是司空见惯,人们用极为低廉的价格即可以买到一幅精美绝伦的画。在当时,只用二十荷兰盾左右就能买到一幅扬·凡是·艾克的作品!(376-377页)但是,即使是在收入低微的境况中,荷兰艺术家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精细的描绘风格,没有让自己的作品变得粗制滥造,关键是因为他们的心灵并没有破裂,手艺人的天职伦理仍旧扎根于意识之中。
在“小型藏书楼与题献”的详细阅读建议部分,关于怎样去观察、理解是什么令法布里蒂乌斯想要描绘那位正在等待的制琴师这个主题,提到了马丁·肯普(Martin Kemp)的《艺术的迷信:从布鲁内莱斯基到修拉的东方艺术中的光学主题》(The Science of Art: Optical themes in western art from Brunelleschi to Seurat,1990),这切实其实是一部有关艺术与光学迷信的首创性著作,研究主题是自文艺再起时期至近代的透视法、色彩学等艺术理论及实践与迷信的彼此影响和推动关系,丰富的文献证据与几百幅图版提供了严谨的论证。对于乐迷,作为音乐学专家的安德烈斯在这份阅读指南中提供的唱片信息可能更为诱人。比如关于享有盛誉的斯韦林克的作品,“我们只需听几张最能展现他天才的灌音便足够了。……经过这套唱片,听众不难感受到斯韦林克的平衡,他的音乐老是更靠近心灵,而非宗教。”(399-400页)作者的渊博知识在全书论述中随处可见,所引述的许多是写作于十六、十七世纪的文献材料,对于研究自文艺再起后期以来的音乐、绘画与迷信状况很有参考价值。
最后还是回到法布里蒂乌斯的《有乐器商摊位的代尔夫特景物》吧。这是他留给美术的音乐遗产——也是留给音乐的美术遗产。在作者的眼中,这幅小小的油画就是十七世纪荷兰的缩影,虽然他写的这些并没有出现在画面上——“在午后新教堂的尖顶投下的暗影中,有织补工、卖木桶的人、赶驴的人、斯韦林克的半音阶体系,另有斯宾诺莎的哲学理论……那幅画里另有东方帆海、坏血病和安东尼·范·列文虎克的显微镜。船夫们在运河上运送蔬菜的身影,维米尔为了画出代尔夫特而走到城市另一边河岸的脚步声,制琴师正用龙血为维奥尔琴染色的双手,磨坊里油花花的轴,惠更斯和笛卡尔的书信,放在碎冰上出售的鲱鱼,码头上缝补船帆的人。”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的是,“大概就在那个读信的清早,或是在某个没法预知的黄昏,有人会买下一把摆在路边摊位上的维奥尔琴或鲁特琴。谁具有这些乐器,谁便能经过音乐来避免或减轻所有的不幸”(389页)。读到这里,真是感到有一种温馨的力量奔涌而出,那就是绘画、音乐与手艺在那个时代叠加在一起产生的美感与温情。
公布于:上海市